马奇——德鲁克之后的顶级管理大师。但其理论和思想在中国传播并不多,学术圈之外,鲜为人知。为了传播其理论和思想,在2016年《清华管理评论》组织众多管理学家转为介绍马奇的理论和思想,以及其思想对中国企业管理的现实意义。有幸采访到马奇本人,同时得到八位管理学家的支持,分别撰文介绍马奇不同的理论和思想,并用其理论重新思考当下的现实问题,精彩纷呈。1 f* G( l( d+ _) F7 X
Z! @) N/ R' O% Q9月30日~10月8日,《清华管理评论》将每天推出一篇文章,首次全文分享给广大读者。欢迎评论,谈谈马奇的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及现实意义。我们将每天选出3位留言的读者,赠阅马奇的那些经典之作、传世之作。
0 n$ l) w) N( P3 ^9 b! u2 K
葛建华 | 文
) C7 U! M; X7 ^$ {* W
7 H4 B2 k! P1 v4 R5 X R
马奇,一位组织学领域的大师,他挑战与颠覆了传统的、主流的组织模型,重建了组织分析的基础。在当下这个新涌现出来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经理人员们面临着大量的未知与不期而至的问题,如何重新思考组织?马奇犀利独到的见解大有助益。
5 ^/ ?0 z& X$ q7 H/ j为什么要读马奇?
: L# ?" H# z, S. A. [
2006年,马奇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提到学术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差别。他说,学者们主要是关注那些形塑管理历史与现实的基本机制,而管理者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则针对特定时空下的个体经验。学术知识难以解决具体和专门情境下的问题;但在新涌现出来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当经理人员们面临大量未知与不期而至的问题时,这些学术知识恰恰变得重要而有用。说到底,它不提供答案,却提供给我们认识(新)问题的思考框架。一定程度上,在互联网技术全面发展渗透、全球化高歌猛进、跨国企业蓬勃扩张、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再读马奇、再思考马奇的学问,也变得必要。
: a) C6 b8 x* F7 _7 c4 A) b, |/ g)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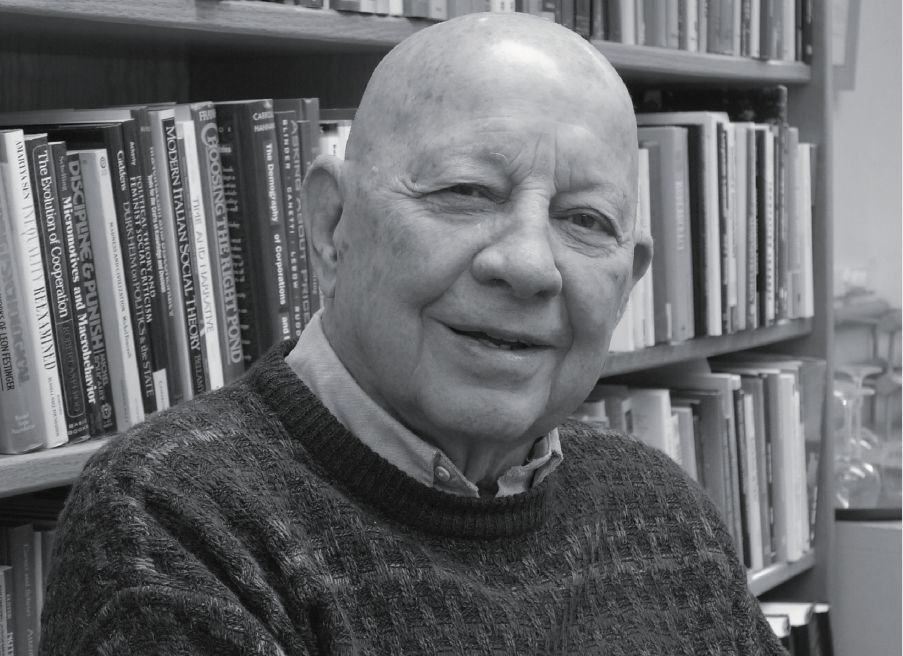 ) c: Y+ F; { y! Y& b" }
) c: Y+ F; { y! Y& b" }
与西蒙、塞尔特等学者一道,马奇是组织学中影响深远的卡内基-梅隆学派的主要创始人。这一学派的重要主张是“有限理性”,即由于人们获得信息及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们的理性选择因而有其局限性。有限理性的基本认识,颠覆了传统经济理性假设下的组织模型。在此基础上,马奇开创性地提出一系列的重要命题。他犀利独到的见解持续荡涤人们关于组织的思考,长久以来被奉为圭臬,成为当今组织分析的基础。
) t: o" V: a. W0 j马奇的独辟蹊径让人叹服和着迷,他对于传统、主流组织模型的挑战和颠覆,一面激荡人们关于学术的“唯美”的想象,一面却又持续逼近深层而被扭曲的现实。无论研究者还是管理者,都能于此受益。
1 `2 h. h- R5 W- I+ g: q+ e/ p组织决策的陷阱
* K/ d2 K% q+ o# h5 N
与传统组织模型所描摹的理性、秩序等大相径庭,马奇直言组织是“有组织的混乱”(organized anarchy),充满“模糊性”(ambiguity)。马奇这样描述我们所处的复杂并让人困惑的组织:
# o! D$ \% g" |- D
“许多事情同时发生,惯例和技术在不断变化,并且令人难以理解;偏好、身份、规则和观点都是不确定而不断变化的;问题、解决方法、机会、情境、人和结果都混合在一起,难以解释他们的联系;不同时点的决策似乎有联系,但却非常松散;提出的问题与解决方法之间的联系似乎也不密切;政策未被执行;决策者在决策时徘徊不前,而且似乎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0 P6 N6 J9 ], T7 X, q9 y
在这样复杂、动荡以及模糊的组织世界里,马奇对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并使用了颇为形象的“垃圾桶”模型来比拟和把握现实中的组织决策。这种弥漫于组织的模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模糊与不一致的偏好。组织中的决策者常常是在行动中觉察他们的目的,而非在决策前已经明了“自己想要什么”。而随着组织的规模与复杂性相伴增长,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之间也容易产生冲突,其实现的优先次序也会随机多变。第二,模糊的技术手段。所谓理性定义中的“手段-目标”的因果关系并不总是明晰的。人们常常只抱有模糊的认知,而在“试错”的学习机制下去获取知识,但却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尽然像理性决策模式所主张的依逻辑思考的决策步骤去解决问题。第三,决策参与者的流动性。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常常来来去去,随时点而变,不同的偏好、利益、冲突等因而被卷入到决策中。由于决策参与者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参与决策者可能前后完全不同,故同样的议题由于不同的人员出席讨论,结论也可能与原先规划完全不同。
' s P! |; y- m3 s6 m: s被模糊性定义的组织,其决策常常决定于四股力量:问题、解决方案、参与人员和决策的机会。它们之间的消长互动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会浮上台面,成为热门的议题,然后进入到决策来试图解决。换而言之,问题、偏好以及解决方案之间并没有紧密的逻辑关联,组织决策是一个被偶然性左右的过程。
8 V$ o$ q0 h0 `3 ]( B) ^
马奇笔下的组织决策中,理性的没落是一种警醒。
: v' Z! }0 ^9 ?* D* W《德意志银行十分钟的悲剧》一文讲述一个令人惊异的故事,引述如下:
; X( ]' w0 N Y# Z. P% h2 X$ m
2008年9月15日上午10点,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消息转瞬间疯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德国国家发展银行10点10分居然按照外汇掉期协议的交易,通过计算机自动付款系统,向雷曼兄弟公司即将冻结的银行账户转入了3亿欧元。转账风波曝光后,德国社会各界大为震惊,舆论哗然。因为此前一天,有关雷曼破产的消息已经满天飞,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应该知道交易的巨大风险,并事先做好防范措施才对。人们不禁要问,短短10分钟里,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导致如此愚蠢的低级错误?
: B9 I( m( S9 }6 j$ R; g首席执行官乌尔里奇·施罗德:我知道今天要按照协议预先的约定转账,至于是否撤销这笔巨额交易,应该让董事会开会讨论决定。
" n$ I/ Y F3 ~) b: `
董事长保卢斯:我们还没有得到风险评估报告,无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8 [! `% N) c9 ~! A9 p
董事会秘书史里芬:我打电话给国际业务部催要风险评估报告,可那里总是占线,我想还是隔一会儿再打吧。
! g% D, b4 d. g国际业务部经理克鲁克:星期五晚上准备带上全家人去听音乐会,我得提前打电话预订门票。
( U9 w& G+ U/ o1 T8 I国际业务部副经理伊梅尔曼: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时间去关心雷曼的消息。
5 u% F+ m2 W: k% U$ {6 h
负责处理与雷曼业务的高级经理希特霍芬:我让文员上网浏览新闻,一旦有雷曼的消息就立即报告,现在我要去休息室喝杯咖啡了。
- ]+ t$ X+ m0 q+ r2 @& B7 n# {4 D9 @# E
文员施特鲁克:10:03,我在网上看到了雷曼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新闻,马上就跑到希特霍芬的办公室,可是他不在,我就写了张便条放在办公桌上,他回来后会看到的。
( `; w* m {4 Z# S+ N. [结算部经理德尔布吕克:今天是协议规定的交易日子,我没有接到停止交易的指令,那就按照原计划转账吧。
- A) p. y6 p0 G6 ~5 J
结算部自动付款系统操作员曼斯坦因:德尔布吕克让我执行转账操作,我什么也没问就做了。
& o9 E8 R! K7 g" v/ t信贷部经理莫德尔:我在走廊里碰到了施特鲁克,他告诉我雷曼破产的消息,但是我相信希特霍芬和其他职员的专业素养,一定不会犯低级错误,因此也没必要提醒他们。
) ^7 J' k D* A5 R j% u2 s
公关部经理贝克:雷曼破产是板上钉钉的事,我想跟乌尔里奇·施罗德谈谈这件事,但上午要会见几个克罗地亚客人,等下午再找他也不迟,反正不差这几个小时。
# H/ m) Z4 Z9 p- |7 m理性的神话,不过是对现实的讽刺。
* P k% P8 ~4 r% `! @8 X组织目标的陷阱
2 b+ h; N8 D! z# E
1962年,马奇提出:企业是一个“政治联盟”,首次将政治分析机制引入到组织研究中,超越了之前在组织研究领域盛行的“理性选择”,也拓展了他和西蒙等的“有限理性”的分析视野,塑造了一个更为逼近真实的组织模型: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都是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进入组织。组织运行和决策因此体现为一个冲突过程、一个政治过程、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博弈的过程,以及一个利益联盟构造的过程。与德鲁克、巴纳德等管理学大师都强调共享的组织目标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不同,马奇的政治视角挑战了一个基本假设:究竟有没有单一的组织目标?实际上,在马奇的政治视角下,任何组织都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合而成。组织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对决策施加影响,决策和决策的实施过程是一个双方或多方“策略互动”的博弈过程,这种“策略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以各方“利益”而不是组织效益最大化为基础。因而,所谓共享的组织目标,实则被分化的、各方利益集团自己的目的所替代。
7 j; t+ ?6 N, I5 N马奇的政治分析视角,使得对目标的设定从“领导者设定组织目标”的判断中跳脱出来,强调领导者本身可能只是利益联盟中多种力量的一支。在多方博弈中,谁的目标能成为组织目标,不是一个设定过程,而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或许是:如果不是领导者,那么谁在控制组织目标?在马奇看来,企业天生就是冲突的场所。现代企业建立之初,就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聚合:投资方、管理层、员工、顾客,包括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等。任何一方在企业治理过程中都会试图通过权力手段(包括:强制、资源依赖、意识形态等)来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此看来,组织本质上都不可能再用单纯的经济学或管理学视角来解释,而必须用政治的眼光来琢磨。这个时候,理性逻辑恐怕得让位于强权甚至暴力逻辑。
3 ^' ]: k4 p; j! ^
前不久,一封《致全体大娘人的公开信》在网上传播。此信正是出自“大娘水饺”创始人吴国强,暴露出品牌创始团队与资方管理团队之间的深刻矛盾。吴国强作为创始人却被拒之公司年会会场门外的情景,不能不说“悲凉”。此类权力争夺的冲突,如俏江南、万科等,多少折射出马奇的组织政治观的犀利!组织不是那一贯温情的奋斗共同体,却是短兵相接、激烈肉搏的权力场。所谓的阴谋阳谋,或许是一种渲染,却更戏谑地直指组织的血肉本质。我们可以被愿景、使命、共同目标所激励,但却不能不思考:我们被谁的权力之手在操纵?
' T0 _; t4 }0 J7 G/ a2 e, m
组织学习的陷阱
+ _2 M! U" L0 V! L2 w# r马奇不断质疑:要不要对学习怀有无条件的热情?与鼓吹学习的流行观点不同,马奇引导我们关注“学习的短视”、“胜任力的陷阱”、“适应与适应能力的悖论”等重要命题。
+ l' u1 c+ q$ e2 K/ U
学习是一个过程,组织在此过程中监控经验,并据此改变行动倾向。经理人的一项任务就是,监控自己的经验并从中学习,另外一项任务就是,组织大家学习并且运用从自身和他人经验当中获得的知识。但这种组织适应过程中却具有隐性的短视。在组织的学习过程中,短期局部看似成功的行动往往被作为“成功”经验复制。而恰恰由于“成功”,经验和胜任力互相积极反馈:越擅长的活动,组织越经常从事;越经常从事的活动,组织越擅长。学习的自我强化导致组织只聚焦于现在的领域,其结果就是组织的某些“特长”被放大,组织变得特别精通能够产生具有即时优势的业务活动。由于组织对自己现有特长和优势的专注和钻研,作为一个学习者,就会越来越疏远其它领域的经验和知识,越来越难应付其它领域的环境变化。当“成功”嵌入到组织中成为经验、知识甚至是规章制度时,这种对于学习的保存沉淀也就可能会成为未来组织适应的桎梏。
! o0 D- W3 t( ]& z$ \4 @
学习作为一种适应过程,也包含两种活动和机制:一是利用,一是探索。利用是指短期之内将既有的想法、技术、战略或知识常规化、完善化、精细化,利用其来努力提高效率。探索则是指尝试新事物,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可以替代旧事物的新事物。组织在这两类活动中分配注意力和资源。对于成功的企业而言,利用性学习的回报显然要比探索性学习的回报更确定、更快、更近,偏向“利用”的组织学习在组织的实际决策和行动中也就更占优势,但也更易招致我们所说的“胜任力陷阱”和“成功陷阱”。
3 { L. T7 a0 {! H
马奇所倡导的组织学习其实是一个平衡:利用与探索的平衡。组织适应既要求利用,又要求探索。专于利用的系统会发觉自己越来越擅长一项越来越接近于废弃的技术;专长于探索的系统永远不会实现其探索的优势,因为即使一个好的想法,也需要在积累足够的胜任力之后才能发挥作用。
# N3 K R; x7 I2 U8 s# g如何实现这种利用与探索性学习的平衡,以及什么状态的平衡是最佳平衡,都是管理者需要关注的。许多人认为可以通过灵活的组织结构设计、独立子单元或部门的设置来构造组织的二元能力。但也有人指出,个体组织一定是短视的。从长期来看,即使存在探索性的单独部门,这些探索性的单元也会逐渐走进“胜任力”陷阱,变成“利用”性学习:如果他们有成功的探索经验,那他们就会遵循那些经验,甚至提炼成为创新法则,其实阻碍了新的环境中的探索。
3 N( i" B# Z# g3 o7 ]: r
成功的陷阱以及学习的困境是每一个企业巨头面临的挑战。创新者如苹果,仍然要思虑iphone极其成功之下却多少有点乏善可陈的尴尬。当下的互联网创业热潮似乎更让“成功”变得触手可及,一批新的基于互联网以及移动终端的创业企业迅速崛起。如何审慎对待自己的成功,或许才是真正的考验。
$ `! T8 U. ?! Z6 i
马奇的深刻和犀利,是学问上的唯美,也是现实中的疼痛。阅读和思考马奇,促使我们更加接近逼真的组织,也迫使我们重新整顿自己的世界。
7 ?$ t3 o! ]1 V4 o. S